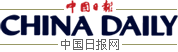中國日報網消息:時隔半年多,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昨日第二次審議保密法修訂草案,此次修訂在諸多方面作出重大修改,涉及到區分國家秘密和商業秘密、上收定密權、設定保密期限以及取消一審草案中保密部門的行政許可權、調查權和罰款權等。
曾多次參與保密法修訂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對此給予很高評價,認為二審草案相對一審草案有很大進步。
保密人員脫密期不得泄密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第二次審議保密法修訂草案,在上次審議中,常委會委員認為管理好涉密人員是做好保密工作的核心,一些部門和公眾也表達了對這點的期待。二審草案對此給予回應。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安民表示,法律委員會經同內務司法委員會、國務院法制辦、國家保密局研究,建議增加相關規定:“涉密人員應當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質和品行,具有勝任涉密崗位所要求的工作能力。”“涉密人員在脫密期內,應當按照規定履行保密義務,不得違反規定就業,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知悉的國家秘密。”
修訂草案還規定,機關、單位應當建立健全涉密人員管理制度,明確涉密人員的權利義務和崗位要求,對涉密人員履行職責情況開展經常性的監督檢查。
秘密期限不超過十年
保密法修訂涉及的關鍵問題即為保密與公開的關系。此次二審草案上收了定密權,并對不同密級的秘密確定了保密期限,此規定有望結束目前保密工作中秘密“一定終身”的狀況。
修訂草案規定:“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規定外,絕密級不超過三十年,機密級不超過二十年,秘密級不超過十年。”
修訂背景
保密法實施20多年面臨多個問題
鄉政府可定絕密級文件
我國現行的保守國家保密法實施了20多年。2009年6月保守國家保密法修訂草案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就保密工作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了修改。
問題1 定密標準不明確
一些常委會委員和部門提出,國家秘密的范圍比較寬泛、定密標準不明確,不便于掌握執行。考慮到秘密事項應當區分國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商業秘密,草案對“什么是國家秘密”作出了明確規定。
問題2 定密過多過亂
目前,我國存在著定密過多、過亂的問題。一個鄉政府也可以定一個絕密級文件。
此前,國家保密局曾在媒體上公開表示,只有先把密定準了,才能做到既保障國家信息安全,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又促進政府信息公開和信息資源合理利用,保障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
湖南省政府辦公廳的一位官員說,不該保密的文件被定了密,顯然給保密工作增加了難度,提高了保密成本。他舉例說,某市委下發的一份關于向先進人物學習的文件竟然也加密,足見保密文件的泛濫程度。
問題3 密級“一定終身”
針對密級的“一定終身”,修訂草案明確,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規定外,絕密級不超過30年,機密級不超過20年,秘密級不超過10年。
問題4 罰款難以制止泄密
對于泄密事件的處理,保守國家秘密法修訂草案此前規定了保密行政管理部門的罰款權。
對此,常委會委員張學忠認為,這種方式“不夠嚴肅”。“這些罰款少的1000元,多則幾千元,且不說這種方式能否起到震懾作用,這種規定在國家層面的法律中出現,顯得不夠嚴肅。”
焦點1 絕密期限擬不超30年
草案規定,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除另有規定外,絕密級不超過30年,機密級不超過二十年,秘密級不超十年。
【解讀】
“秘而不解”阻礙社會進步
背景:目前的保密法沒有規定保密期限,草案在一審時,陳斯喜委員即提出應確定文件保密期限。而在草案征求意見中,財政部和國家糧食局等亦都提出設立秘密期限的建議,國家糧食局的建議和目前草案規定一致。
公眾對保密期限的要求則更高一些,認為絕密級不超 20年、機密級不超10年,秘密級不超5年。
二審草案首次規定了國家秘密的保密期限,此規定有望結束國家秘密一定終身的問題。
曾多次參與保密法修訂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表示,“過去秘密往往是一定終身,只定不解。”而比如外交部等解密了一些文件,但沒有制度,難以常態化。保密信息一定終身“阻礙了社會進步,尤其是阻礙信息化的發展,檔案法里規定了30年,這次也吸收了檔案法的規定和國外的普遍做法。”
不過目前草案規定的保密期限并非絕對,草案同時也規定了,對保密期限需要延長的,應當重新確定保密期限。
對于保密期限留一個“口子”的規定,周漢華認為可以理解,國家秘密情況復雜,確實有一些秘密事項,到了30年還不宜公開,“這不僅中國有,國外也有,重新定密的制度設計是個國際通例。”
但是如何防止這個規定被濫用,致使重新定密本來是例外,實施中卻變成了慣例,周漢華認為首先取決于執法者的法律意識,不能將例外情況變成常態,或者濫用這一規定。但僅此還不夠,還需要有制度,比如社會主體認為秘密到期應該解密,或者公開更有價值,如果保密單位濫用這款規定,可以主張權利,進入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的程序,進行審查。
不過他認為這些制度設計不是保密法能解決的,行政訴訟法、行政監察法、公務員法都要起作用,他解釋,定密行為是可以接受司法審查的,因為定密主體不是保密部門,而是具體部門,“這些政府機關作為訴訟的被告是沒問題的,行政訴訟法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也都規定了可以訴訟。”
對于是不是有必要在保密法中明確對此的司法審查,周漢華認為保密法即使不明確規定,根據行政訴訟法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都是可以起訴的,不過二審草案刪除了此前草案涉及的保密管理部門的行政許可權、調查權和罰款權,周漢華認為,由于中國特殊的體制,國家保密局和中央保密辦是一個機構,保密局的行為還是內部行政行為,不對社會主體發生權利義務影響,“保密行政部門的行為還是不能進入訴訟為好。”
焦點2 秘密級別不能隨便定
草案規定,中央國家機關、省級機關及其授權的機關、單位可以確定絕密級、機密級和秘密級國家秘密;設區的市、自治州一級的機關及其授權的機關、單位可以確定機密級和秘密級國家秘密。
【解讀】
縮小定密主體節省行政成本
背景: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安民向常委會作保密法修訂草案修改情況匯報時表示,這是吸收了常委委員、部門和地方的意見,旨在解決定密過多過濫。
周漢華此前參加全國人大法律委、內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聯合組織的專家座談會時,亦曾建議上收定密權,周漢華表示,中國保密制度一直以來在定密權上放得非常開,“開到任何單位甚至單位內部的科室都有定密權力,這和國際通行做法比不合適。”他解釋,國家秘密是國家需要保護的,泄露后會造成國家安全、政治、經濟嚴重危害的事項,而中國放得太開,導致定密過濫。一些定密人員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為了規避責任,都給定成國家秘密,而且一定終身,這同時也帶來一個問題,定得太多了,該保的也沒保住。”
周漢華認為上收定密權能有效解決定密過多、過濫問題,并會推動信息自由流動,推動國內經濟和社會信息化以及促進信息產業發展等方面也有重大意義,同時,“把真正要管的管好,該保的保住,能產生雙贏或者多贏的效果。”
根據二審草案對此的規定,將會大大縮小現在的定密主體,“中國的設區市,自治州有600多個,而縣有3000多個,原來定密主體是海量的,現在可以節省大量的行政成本。”
對于這個制度上的重大改變,周漢華認為今后還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他建議隨著保密制度的發展,在目前定密主體的基礎上,還可以進一步明確化,或者進一步縮小定密主體的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