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著名經(jīng)濟(jì)學(xué)家李稻葵看來,諾貝爾獎的歐洲背景也多少影響著獎項的授予:
李稻葵: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的中心到目前為止還是在美國,這個獎項是歐洲人占主導(dǎo)的,他評出的得獎人讓內(nèi)行人有點哭笑不得。一般得這個獎的人,我觀察有這么幾個條件,第一確實有獨特的貢獻(xiàn)。第二個要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個影響力不僅體現(xiàn)在對整個學(xué)界的影響力,可能還體現(xiàn)對歐洲委員會的影響力。第三個,跟這個相關(guān)的,人緣好的人容易得獎。
有學(xué)者認(rèn)為,目前國內(nèi)更側(cè)重于對當(dāng)下現(xiàn)實問題的分析與探討,對應(yīng)用性的學(xué)科有著更多的關(guān)注,而少有純理論研究者進(jìn)行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研究。那么中國學(xué)者什么時候能夠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
李稻葵一直主張要有一顆平常心。5年前的今天,李稻葵在哈佛期間的導(dǎo)師馬斯金與其他兩位美國經(jīng)濟(jì)學(xué)家一同獲得2007年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而馬斯金在得知獲獎后照常與博士生討論論文的故事早被傳為佳話:
李稻葵:馬斯金教授是一個超級冷靜,超級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者,他對榮譽性的事情看的很淡。他第一個反應(yīng)是終于松了一口氣,因為多年來力推薦的另一個90歲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學(xué)者終于得獎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德高望重的學(xué)長,對于自己得獎沒有感覺。得獎前一年,一位學(xué)者問他有沒有可能得諾貝爾獎,他說這個事情不想,一想起來就讓人的包袱太重,難以釋懷,這個問題連想都不要想。
馬光遠(yuǎn)則坦言,雖然中國不乏優(yōu)秀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者,但整體上中國的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研究仍處于追趕階段,未來任重而道遠(yuǎn):
馬光遠(yuǎn):未來中國經(jīng)濟(jì)學(xué)人如果真的對中國經(jīng)濟(jì)變遷,對中國改革開放30、40年來的一系列成就有一套獨特的解釋的話,也不排除有獲諾獎的可能。但是目前來我認(rèn)為我們?nèi)狈σ粋€整體的團(tuán)隊,這么多年形成整體團(tuán)隊的美國、英國等在經(jīng)濟(jì)學(xué)方面的研究已經(jīng)形成整體的高度,也就是說排在第一梯隊的人是比較多的,而我們排在第一梯隊的人是鳳毛麟角的。我認(rèn)為就整體而言,我們離沖擊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還是有很大差距。
 范爺?shù)怯罂?/a>
范爺?shù)怯罂?/a>
 揭秘大牌酒店帝國
揭秘大牌酒店帝國
 女星逆生長超極限
女星逆生長超極限
 時尚達(dá)人奢華私藏
時尚達(dá)人奢華私藏
 河北現(xiàn)“羊堅強(qiáng)”天生倒立行走
河北現(xiàn)“羊堅強(qiáng)”天生倒立行走
 千年后人類模樣
千年后人類模樣
 大熊貓 大道理
大熊貓 大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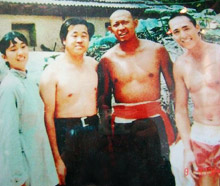 莫言曾為張藝謀鞏俐"做媒"
莫言曾為張藝謀鞏俐"做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