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作者下筆動輒洋洋萬言,但自我重復的痕跡顯而易見;有的作家謹慎克制惜墨如金,不出手則已,出手則不凡。阿來,無疑屬于后者。
從1994年開始寫長篇處女作《塵埃落定》,至今20年來,阿來還有兩部長篇《空山》和《格薩爾王》已出版。《空山》是表現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中藏族鄉村文化的變遷過程。憑借這部小說,阿來于2009年獲得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2009年阿來出版的《格薩爾王》,用現代小說方式重寫了史詩“格薩爾王傳”。
在作品數量上,阿來算是“低產”,但是從作品質量看,阿來用作品在讀者心中的分量證明了,他的文字,從歷史到現實,從虛構小說到非虛構歷史,都做到了言之有物,技藝非凡。
對于即將到來的2015,阿來對華西都市報記者說,他將拿出這幾年自己積累的行走和思考成果,以作品的形式與讀者分享,“至少要出5本新書。此外,在延續多年高原行走、地理文史考察的同時,我會拿出較多的時間用于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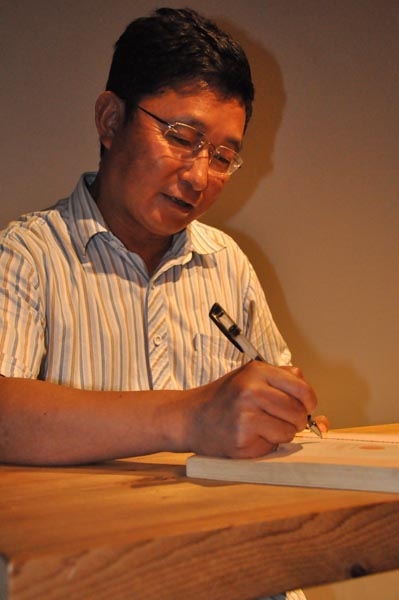
作家阿來
關心歷史不是講傳奇故事
近期的阿來,又“聽”到了他內心寫小說的召喚,連著寫了兩部中篇小說。早在2014年8月趁采訪之機,華西都市報記者也在阿來的筆記本電腦上看到這兩部中篇小說其中一部的開篇,文筆一如既往地簡潔、明凈。阿來說,這兩部中篇,按照計劃將在2015年年初的《人民文學》《收獲》上首發。
華西都市報記者(下稱記者):您這兩部中篇小說中,一個線索是“蟲草”,另一個是“松茸”。這兩個可都是現在炒得很紅的商品啊。這是想表達您對一些現象的批判嗎?比如在一些鄉土小說中所表達的,外部世界對傳統地區生活的沖擊?
阿來:如果僅僅想表達這些,那意義不大。小說家的主要職責不是批評誰,而是用藝術的手法,能啟發讀者一起思考。我一直在觀察,像蟲草和松茸這些大自然的物種,借著一個商業鏈條,身價倍增。而它們的原產地居民,并不是主力消費群的身份。在我看來,這真是現代都市瘋狂拜物教的生動象征。我也在思考:對物種的過度開采,造成生態破壞,這個代價該如何評估?這種現象背后的根源在哪?
記者:您當下思考的成果是怎樣的?
阿來:我想,改變一個地方的經濟結構,保護生態,可能還不光是政府的責任。過度的商業推廣,瘋狂的商品消費,也是讓傳統資源被城市消費綁架的重要原因。在一整套商業流程模式越來越圓熟之時,有沒有人反省:要不要這樣做?商人賺得巨額利潤之后,應該有一顆對傳統資源的敬畏之心,或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對原產地地區的反哺機制。
記者:您此前的作品,比如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或者非虛構《瞻對》多是離當下較為遠一些的歷史題材。而現在你的寫作題材偏向現實社會生活題材,目光好像更專注于當下現實。這是自然的還是有意的轉變?
阿來:我以前寫歷史,從來也不只是為了寫歷史。不是為了講個傳奇故事,或者做幾場熱鬧的百家講壇。我是基于現實關懷,去歷史深處找源頭。畢竟,現實是沿著歷史的脈絡走到現在的。歷史與現實始終交織。寫《塵埃落定》《瞻對》這些,將歷史理清楚后,我的寫作,自然想要離現實更近。
他將集中呈現“高原行走”
阿來不是那種“書齋里的作家”,這些年來,他多次在川藏線上行走,祁連,地理山川,歷史人文,奇花異草都是他的尋訪對象。
記者:這幾年,您都去高原上做植物考察,高原植物攝影。這些考察的成果,什么時候以作品的形式,與讀者見面?
阿來:2015年,我就是要陸續出我這些年在青藏高原考察的植物學成果,大概是三到四本的作品系列。不過我想說的是,青藏高原除了是一個大的自然存在之外,還是一個大的歷史載體。我還正在寫一些這些年行走高原,對沿途人文歷史和現實生活進行綜合思考的文章系列。
記者:這些隨筆應該跟《瞻對》那種非虛構歷史體裁相似吧?目前進展如何?
阿來:比《瞻對》的寫法更自由。準確的文體定位,意義并不大,重要的是寫得好不好。我寫的這些文章,主要是這些年來,我以川藏線為核心,在高原上進行大面積行走、思考的文學結晶。我已經跟一個騰訊文學簽約,這些文章在一個固定專欄“大家”上首發連載。。
記者:看來2015年將是您的作品出版集中“爆發”的大年啊!
阿來:我初步算了一下,2015年我至少要出5本新書。這也是這么多年來我很少出新書,因而造成的一個積累吧。
不掩飾對世事的真實反應
2014年8月,阿來的長篇非虛構作品《瞻對》在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類別的終評階段中,獲0票。阿來公開對這種結果表示質疑。這種坦率不掩飾的做法,成為文化圈當時的一大焦點。
記者:當時您直接說出“我抗議”,現在想起來,會感到后悔嗎,比如說當時其實可以謹慎、委婉一點?
阿來:我不會后悔。當時表達質疑和抗議,是自然而然的真實反應。我從不掩蓋自己對世事的真實反應。
原標題:2015阿來迎來新作“大爆發”